来源:广西民族报
发布时间:2019-1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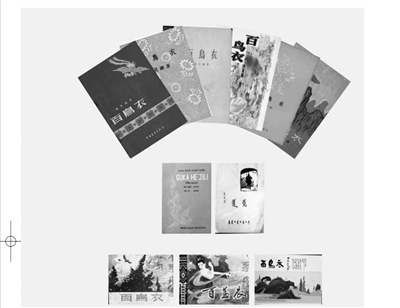
▲韦其麟作品《百鸟衣》出版的各种版本。
【作家简介】
韦其麟,男,壮族,1935年出生,当代著名诗人,曾任广西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五、第六届副主席。著有叙事长诗集《百鸟衣》《凤凰歌》,诗集《寻找太阳的母亲》《含羞草》《苦果》,散文诗集《童心集》《梦的森林》《依然梦在人间》,诗文集《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韦其麟卷》等。曾先后获得全国少数民族第一、二、三届文学优秀作品奖。
进入当代以来,韦其麟作为壮族诗人的重要代表,多次出现在文学史与诗歌史的写作中。韦其麟的诗被译为英语、俄语、日语等多国语言,极大地增强了其作品的传播与影响力。前苏联评论家奇施柯夫曾将韦其麟的《百鸟衣》与长诗《阿诗玛》以及其他民族的童话与传说并置起来,认为“韦其麟的长诗《百鸟衣》在这些作品中占有自己一定的地位”。
韦其麟的诗歌创作立足于广西地理空间,悠久、厚重的壮族文化赋予了该地理空间以独特的民族色彩。从根本上说,他的写作包含了两个主体性要素,一是对壮族民间文学的深刻诠释,二是对广西地域文化的集中再现。此两者均生成于广袤而又多样的广西地理空间之上,不仅凝聚了壮族人民对本民族历史的思考,而且饱含着他们对广西地域的深厚情感。
诗语意象表现之一:地域性的直观展示
对于少数民族诗人而言,浓郁的地域性通常能够成为其重要的创作标识,而地域文化本身则作为构筑文学地理空间的本体性要素,为研究者们所重视。韦其麟在其诗歌写作中有着鲜明的地域性呈现,其诗作中经常出现“百鸟衣”“花山壁画”“桃金娘”等独具壮族文化特色与广西地域特征的地理意象。这些意象一方面凝结了他对壮族文化的深刻思考,另一方面则饱含着他对广西地域的真挚情感。韦其麟曾谈到了“地域景观”对写作《百鸟衣》的重要影响:“当我要向读者介绍古卡家时,一闭上眼睛,那些优美的情景就呈现在眼前了。山坡呀,溪流呀,鸟呀,果子呀,甚至也听到了那回响在深山中的优美的山歌声。这使我很顺利地把南方山村的色彩描写了出来。”而《百鸟衣》中也多次呈现了“南方山村的色彩”,如诗句:
“绿绿山坡下,/清清溪水旁,/长棵大榕树,/像把大罗伞。//山坡好地方,/树林密麻麻,/鹧鸪在这儿住下,/斑鸠在这儿安家。春天的时候,/满山的野花开了,/浓浓的花香呀,/闻着就醉了。//夏天的时候,/满山的野果成熟了,/甜甜的果子呀,/见着口水就流了。//秋天的时候,/满山的枫叶红了。/红叶随风飘呀,/蝴蝶满山飞。//冬天的时候,/小溪仍歌唱,/松林仍旧青,/像春天一样。”
“百鸟衣”这一壮族地理意象正是在“南方”的地域景观中生成,这既表现出韦其麟对“山坡”“溪水”“榕树”“鹧鸪”等自然景色的赞美,又包含了他对山中“春”“夏”“秋”“冬”四季优美景观的赞叹。作为长诗《百鸟衣》主导意象,“百鸟衣”不仅直接建构起了故事的整体,而且其自身带有丰富的壮族文化内蕴。“百鸟衣”尽管在长诗中出现的次数很少,但它的作用不可或缺。从依娌被土司抢走时对古卡的提醒——“古卡呵古卡,/心理别害怕,/你去射一百只鸟做成衣,/等一百天找我到衙门里!”到“百鸟衣”的生成——“一百张雉鸡皮,/张张一样美,/缝成一件衣,/羽光亮闪闪”,再到古卡依凭借“百鸟衣”将土司杀死,故事被不断推向高潮,独具壮族特色的民间文化也集中传达出来。
“花山壁画”作为韦其麟诗歌中重要的壮族地域风物,其自身带有较强的历史性,寄寓着诗人对壮族文化历史的思考。如在《花山壁画之歌》一诗中,韦其麟通过歌颂“花山壁画”,集中表现出了他对“义军”英勇精神的赞美之情——“庄严的崖壁含着悲愤,/高高托起壮丽的图景;/英雄的山头并没有沉沦,/不屈的队伍又重现踪影。”这种将自我情感寄托于民族风物的写作,具备了壮族文化的传承意识。此外,“花山壁画”还体现出了一种“寻根”的气质。因此,韦其麟通过描绘“花山壁画”,深刻地诠释了他对广西地域文化内涵的理解。
又如“桃金娘”是壮族特有的花,其本身不仅带有着鲜明的壮族地域色彩,而且又饱含壮族人民的热情。在韦其麟看来,“桃金娘(亦名逃军粮)是壮族地区随处可见的一种普通而美丽的小灌木,春天它以满树满树粉红的繁花打扮着壮族的山山岭岭,夏日又献出一树树甜蜜的紫色的果子。壮族人民对桃金娘非常熟悉而又亲切……”这不仅充分昭示出“桃金娘”之于壮族地区的特殊作用,而且也强调了有关它的书写的重要性。韦其麟的《四月,桃金娘花开了》一诗,借助对“开遍了壮家的山山岭岭”的桃金娘花的描写,着力凸显了“姑娘”崇高的革命精神。诗中的“姑娘”最终化身为桃金娘花——“雨过了,人们把姑娘呼唤,/不见了,再听不见姑娘的回应。/只见满山长起绿绿的小树,/小树开满了红花多么鲜艳。/天晴了,人们把姑娘呼唤,/不见了,再看不见姑娘的身影,/只见漫山的小树结满果子,/紫红色的小果像蜜一样甘甜。”——她为着革命事业而不惜牺牲自我,给予后来者以极大的精神砥砺。
诗语意象表现之二:民族性的真挚书写
韦其麟在随后的写作中也并未抛置其本有的“民族性”,并且呈现出了不断强化的姿态,这对于当下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具备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就具体的写作来看,韦其麟对于民族性的展现主要通过“神话意象”“英雄意象”来完成,这些意象一方面植根于丰富多彩的民间神话传说,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对近、现代英雄革命斗争的描摹上。
在创作初期,“民族性”几乎成为韦其麟的唯一源泉,他也由此塑构出了鲜明的民族性意象。如在《玫瑰花的故事》中,“玫瑰花”这一“神话意象”摆脱了一般性的西方文化内涵,而被诗人赋予了鲜明的壮民族特征。该诗通过叙述尼拉与夷娜之间的悲剧爱情故事——二者因反抗国王和王子的“霸权”,最终“拥抱着撞向石台”——最终生成了“玫瑰花”这一“有刺的奇花”。由于故事本身带有着强烈的壮民族文化内蕴,在此基础上所生成的“玫瑰花”则自然具备了鲜明的民族性特征。正如诗中所写:“时光像万丈瀑布哗啦啦地倾泻,/春连着夏呵,秋去冬来又一年。/那堆黄土忽然长起了一枝有刺的奇花,/殷红的花瓣绿绿的叶,/馥郁郁的花香溢满园。/‘玫瑰花’——人们给它安上名字,/就从那时候起哟,世界上才有了玫瑰花。”又如《百鸟衣》中,韦其麟围绕着“百鸟衣”这一“神话意象”,书写出了独具壮民族特色的民间文化传说。诗人将“百鸟衣”作为“神衣”来再现,极尽了其所具备的神奇力量,如诗句“你看羽光亮闪闪,/百鸟衣是件神衣,/九洲里头找不着,/寻遍四海难得到”“穿了百鸟衣,/老头也变得后生俊俏;/穿了百鸟衣,/姑娘见了心欢就会笑。”等。而这一具备着“神力”的“百鸟衣”最终帮助古卡战胜了邪恶的土司,这同时暗含着壮族人民对于困扰其生活的“土司”制度的反叛。
韦其麟在1984年所作的长诗《寻找太阳的母亲》中,也直接呈现出了壮族古老传说的影响。韦其麟循着这一“永远年轻而又非常古老”的壮族传说,书写出了壮族的“逐日神话”。本质上看,该“神话”带有着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变构性质。诗中的这位“年轻的孕妇”,为着满足乡亲们“对光明的殷切的渴求”与“对温暖的深沉的想望”,兀自走向了寻找太阳的路途中,这使得“母亲”与汉族逐日神话中的“夸父”形象等同,但韦其麟又对此进行了自我的变构。因为诗中的“孕妇”在阐释自己“逐日”理由时说:“当我死去,还有我的儿子/继续我的道路,走向太阳。”由此,“母亲”的形象中也融入了“愚公”的精神特质。可以说,韦其麟以其出色的艺术想象力实现了对民间文学的创造性思考,营构出了独具壮民族特色的“逐日神话”。
如果说《玫瑰花的故事》《百鸟衣》《寻找太阳的母亲》等诗歌中建构出了壮民族特征鲜明的“神话意象”,那么《平天山传奇》《郁江的怀念》《红水河边的传说》《凤凰歌》等诗,则将视域投向了壮族近、现代的斗争生活上,由之凝构的“英雄意象”则与壮族人民的英勇精神紧密联系起来。如《平天山传奇》歌颂了太平天国时期壮族农民领袖黄鼎凤领导的农民起义,《郁江的怀念》书写了郁江自太平天国到新中国这段时期的丰富历程,《红水河边的故事》则歌唱了赤卫队与人民共同抗击敌人的英勇气概……而其长诗《凤凰歌》则立足于新中国成立前壮族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的战斗生活,在塑造达凤由壮家孤女成长为游击队女英雄的过程中,呈现出了壮族人民奋勇抗争的决心与勇气。
民族性不仅作为韦其麟诗歌写作的重要坚守,更成为少数民族诗人理解本民族文化的一把“钥匙”。韦其麟对于壮族文化、生活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他与壮族民间文学之间更是形成了双向的互动关系,这就决定了他对壮民族特征的诠释更具创造性,使其立足于民族性的诗歌写作也更为自然与生动。
诗语意象表现之三:文化性的深刻再现
民族文化对于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来说影响深远,它通常作为后者写作的源泉而存在。就此而言,壮族文化对韦其麟的诗歌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韦其麟曾对以花山壁画、铜鼓为代表的壮族文化,表达出了极强的自豪与认同感。从韦其麟的写作历程来说,无论是在写作初期对壮族民间故事、传说的直接借鉴,还是新时期以来对民间文学的自觉融入,其创作中均有着壮族文化的影子,而这种独特的文化性主要是通过“河”“动物”等诗语意象来呈现。这些意象一方面凝结了韦其麟对于壮族文化的深刻思考,另一方面则饱含着他对广西地域的真挚情感。
韦其麟的诗歌中首先建构出了以红水河、郁江等为主体的“河”意象,这种意象带有着文化原型的性质,其中融构的是韦其麟对壮族历史与现实的理性沉思。如叙事诗《红水河边的传说》中,韦其麟书写了党领导的赤卫队与人民一道,在“红水河”边与“敌军”斗争的故事,诗句“万山隐在暮色中,/眼前景色有多美://一轮明月上山顶,/万片银波落河心。//银波托着小渔船,/此时已过千重山。”在再现“红水河”优美景观的同时,真情地歌赞了壮族人民的英勇与智慧。而在抒情诗《红水河从烈士碑前流过》与《红水河——永不苍老的河》中,韦其麟将自身对于“红水河”的真挚情感和盘托出,其中既包含了他对红水河边英勇牺牲的“烈士们”的崇高敬意,又有着对由“红水河”所凝聚的光辉形象与高尚品格的真情歌唱。在诗句“红水河,/远方——你的名字消失了,/而你是不会消失的,/红水河,/岁月一样永不苍老的河,/时间一样永无干涸的河”(《红水河——永不苍老的河》)中,韦其麟将“红水河”与“岁月”“时间”同构起来,暗喻了由“红水河”所凝构的壮族历史与文化的永恒性。又如《郁江的怀念》中,韦其麟一方面通过描绘郁江的优美景观,展现出了他对郁江自然之美的热爱;另一方面,诗人经由对这条自太平天国时期开启的历史意义上的“郁江”的描摹,寄寓了他对壮族历史文化的无限感慨。
其次,韦其麟在散文诗中建构出了以“动物”为主体的文化意象群,表达了他对丑恶社会现实的揭示与批判。以“动物”为主体的意象群的建构体现出了韦其麟对于广西地域文化的独特情感。诗集《梦的森林》充斥着对动物的“拟人化”描摹,韦其麟运用拟人化的寓言笔法,集中地表达出了自身对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名利”“谎言”“世故”“虚名”等丑恶现象的批判与鞭挞。而在诗集《依然梦在人间》中,韦其麟延续了《梦的森林》的“拟人化”笔调,他在《种鸡》《猴子》《蛆之歌》《鼠的抗议》《苍蝇的轻蔑》等诗歌中,将写作的重点投射到有着不良品行的动物身上,并通过对它们丑陋行径——如种鸡的欺软怕硬,猴子的自欺欺人,蛆的得过且过,老鼠的无理抗议等的审视,生动地诠释出了他所持有的社会批判性。
总之,韦其麟的诗歌创作不仅在少数民族文学史,而且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均有着重要的诗学价值。他在曲折而漫长的诗歌创作生涯中,逐步型构出了独特的文学地理空间,这种空间正承载于其诗中所凝构的诗语意象内。笔者通过探究韦其麟诗中的诗语意象,不仅有力地窥探到了其诗歌所展现出的浓郁的地域色彩,而且真切地体悟到了他对民族性的执著坚守。与此同时,韦其麟的诗歌创作植根于悠久的壮族历史文化之上,这使得诗语意象在凸显壮族文化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层面,同样具备着鲜明的话语优势。
作者简介:钟世华,1983年生,山东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南宁师范大学文学创作二级。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与评论,在《南方文坛》《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著有《穿越诗的喀斯特——当代广西诗人访谈录》,主编有《广西诗歌地理》,编著《文学桂军研究资料丛书.韦其麟研究》,曾获广西第十五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等。
编辑:实习生 黄红鑫 mzb